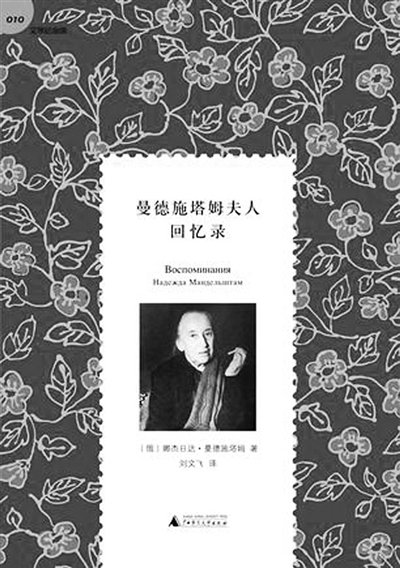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作者: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雅典到俄狄浦斯的故乡忒拜时,已是深夜。那是9月25日晚,古城中三个旅馆全部客满,这个悲情城市以婉拒的方式表达了对投宿者的怜悯。于是,我们重新发动汽车,穿过茫茫黑夜,赶往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的故乡。凌晨3点,抵达丽瓦蒂亚。我像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梦游般被领到女神的泉水旁——“三重的祝福,那个名字谱进歌中的人,/一首被命名增光的歌 /在其他歌中会存活得更久长,/它佩束的标志性头巾, 使它免于遗忘和失去感觉……(曼德施塔姆《无论谁发现马蹄铁》)”。
个人记忆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这样一大批“文化遗孀”在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死去后,充当了一个民族记忆巨大而悲惨的储存器。
这样的诗句,预示着什么?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发生了什么?由谁来讲述历史?当记忆女神敲击我的天灵盖时,我自然会想起诗歌这匹“使它免于遗忘”的、“来自黑暗、比黑还要黑、却不能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马”(布罗茨基诗《黑马》)。
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有着多得可怕的、稍不留心便能毙命的机会,其中之一就是:“在我们这里会因为诗歌而杀人”。因为,那里的诗人有着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对知识分子的判断:一个人对文学和诗歌的态度。“在我们这里,诗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它让人们惊醒,它塑造人们的意识。”这便是独裁者杀人的理由。
令我备受折磨的痛苦阅读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之“五月之夜”开始,从那个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丈夫从邻居家只借到了一枚鸡蛋招待从莫斯科赶来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始——而他们信任的翻译家怀着告密者阴暗的惶恐坐在房间的扶手椅上;从穿风衣的秘密警察的“深夜行动”开始,从对“全苏范围的无家可归者”的逮捕开始——记忆女神握着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的手,以确保它在腥风血雨的沉重往事的碾压下不至于变得粉碎——开始记忆的书写——无论谁握住这支笔,都会像狂风中的芦苇那样剧烈地颤抖。
1934年5月16日晚的秘密搜捕结束后,曼德施塔姆被警察带走。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房间,阿赫玛托娃对娜杰日达说:“您要保持体力。”也就在那时,娜杰日达明白了:“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只得为此保持体力。”
布罗茨基在纪念娜杰日达的悼词中写道:“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这样一大批“文化遗孀”在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死去后,充当了一个民族记忆巨大而悲惨的储存器。虽然,娜杰日达晚至六十岁才开始写回忆录,即便在那个时候,她仍然处于噩梦尚未完全结束的恐惧之中。但这并不影响她几乎绝望地提到了在斯大林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的事实。因此,回忆录的出版,同样也招致了同代人的攻讦。因为除了死者和幸存者,沉默几乎是全体的耻辱。但是,在尸体面前,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呢?娜杰日达所能做的就是——“她的谴责从自责开始。”
这甚至不是政治。这是顽强的记忆在和现实对表,是千疮百孔的时间在与遗忘肉搏。任何遗忘都有可能使历史消逝,抹去血渍,毁灭生命的印迹。历史教科书不会提到一个人如何慢慢死去的细节,但是,个人的历史记忆却能。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张纸片,都能映出那个时代可怖的面孔。在娜杰日达的笔下,文字恢复了记忆,重构了时间,那些遍布朋友、熟人之间的告密者、奸细、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均不认为他们的牺牲品有朝一日会复活,会重新开口。”——这正是记忆在个人那里对历史的伟大贡献,它不仅仅属于曼德施塔姆,它也属于俄罗斯,属于整个人类。
斯大林时代的诗人
“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
且看“惩处机构”要消灭的目标吧: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等等。在这样一份名单前,曼德施塔姆嘲讽斯大林的那首诗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就不奇怪了。须知在那个年代,连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都说:“我们的孩子最爱斯大林,其次才是爱我。”在对斯大林绝对服从的背后,是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流放、苦役、集中营、随意的抓捕,成千上万俄罗斯的知识精英、普通劳动者的死亡毙命。
别尔嘉耶夫有段痛彻心肺的话:“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它把整个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是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布罗茨基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更是“革命”的对象。我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阿赫玛托娃的前夫、诗人古廖夫被枪杀,儿子被关进集中营;茨维塔耶娃回国后贫困交加,上吊自杀……
卡夫卡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布罗茨基在为曼德施塔姆诗集所作序言中写道:“诗人惹出了麻烦,往往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是某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是对整个现存体制提出疑问。它的敌人自然也是成比例地增多。”那么,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受尽折磨最后死于集中营,并不完全因为一首讥讽了斯大林的诗,更不是因为给了作家阿·托尔斯泰一个耳光。斯大林自然恼羞成怒于自己在诗人笔下呈现出一个暴君丑陋的形象,但不可置疑的是,诗人对于美学举重若轻的创造力,对于精神活动热切的催动和启迪,对于威权统治陈词滥调的公然挑战,构成了对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独裁政权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的威胁——“正是因为如此,那把旨在将整个俄国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
写作者向记忆立下的誓言
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并非流水账般的记录,它显示了娜杰日达有对时代邪恶力量清醒的判断力,有对身边事物机警的敏感。
我们不可能依赖更多尚未解密的苏联文件,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个国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遭遇的可怖细节,但已解密的文件让我们得知,在此期间,有几百万人遭到镇压。抽象的数字后面,是无数活生生的人、他们破碎的家庭、绝望的心灵,以及生不如死的幸存者的记忆。整个这段历史的细节,留在丈夫被枪毙、或被折磨致死的诗人妻子、四处躲藏的思想者、爱好文学并偷偷背诵诗句的普通人的记忆中。但是,娜杰日达知道,记忆也会死,因为人最终会死去,于是,我们今天才能从这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从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些可怕的记忆中,了解到那段恐怖岁月里俄罗斯所遭受的苦难。
固然我完全赞同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中对诗人遗孀所作两部回忆录给予的极高评价,但这些评价多是基于对曼德施塔姆、对俄罗斯文化的意义而言。我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娜杰日达“被伟大的诗歌将她‘踹进了’散文”的说法,也不同意他所说娜杰日达是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两位大诗人的“产物”——在我看来这是不公正的。不能因为娜杰日达“诗人的遗孀”这一身份,而抹杀了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事实。她写下这些文字,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诗人的爱情,更有着一位有教养、有良知、也有文字表达能力的作家的自觉和天赋才情。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并非流水账般的记录,这些既恐怖、又令人忍不住悲愤之泪迸溅的呕血之作,显示了娜杰日达有对时代邪恶力量清醒的判断力,有对身边事物机警的敏感,有苛刻的自我审视,有无情的揭示,也有对文学、对语言极为难得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我不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这些还需要别的什么。
一想起人类是容易遗忘的一个生物种群,绝望便油然而生。如果没有文字,没有创造文字的那些大脑,没有记忆,人类与兽群无异。娜杰日达写得清楚:惩处机构的工作目的是“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等等。在我看来,这部回忆录仍然在在世界各处,被许多人续写着。
回想起本文开篇在记忆女神深夜洞窟前的情景,我还记得水声轰响着透明的幽静。四周波光粼粼,我似乎坠入了一个无生无死的世界,密不透风的光和黑暗交织的世界。双手掬起冰冷的泉水一饮而尽——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作为一个不被允许遗忘的诗人,一捧泉水,就是写作者向记忆立下的誓言。
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作家,翻译家。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十九年间,娜杰日达不得不面对丈夫的两次被捕。六十年代初,娜杰日达开始撰写回忆录,反响巨大。